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 是一种精神和行为 障碍,可能因暴露于创伤性事件而发展,例如性侵犯、战争、交通碰撞、虐待儿童、家庭暴力或其他威胁关于一个人的一生。症状可能包括与事件相关的令人不安的想法、感觉或梦境、对创伤的精神或身体痛苦相关线索,试图避免与创伤相关的线索,一个人思考和感受方式的改变,以及战斗或逃跑反应的增加。这些症状在事件发生后持续一个多月。幼儿不太可能表现出痛苦,而是可能通过游戏来表达他们的记忆。患有 PTSD 的人自杀和故意自残的风险更高。
大多数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不会发展为 PTSD。经历过人际暴力(例如强奸、其他性侵犯、被绑架、跟踪、亲密伴侣的身体虐待以及乱伦或其他形式的儿童性虐待)的人比没有经历过性侵犯的人更容易患上PTSD基于创伤,例如事故和自然灾害。那些遭受长期创伤的人,例如奴隶制、集中营或长期家庭虐待,可能会发展为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C-PTSD 与 PTSD 相似,但对人的情绪调节有明显影响和核心身份。
当咨询针对有早期症状的人时,预防可能是可能的,但在向所有遭受创伤的个人提供时无效,无论是否存在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是咨询(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SSRI或SNRI类型的抗抑郁药是用于 PTSD 的一线药物,对大约一半的人有益。药物治疗的益处少于咨询所见的益处。目前尚不清楚同时使用药物和咨询是否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法具有更大的益处。药物,除了一些 SSRI 或 SNRI,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它们的使用,并且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情况下,可能会恶化结果。
在美国,大约 3.5% 的成年人在某一年患有 PTSD,而 9% 的人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发展为 PTSD。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特定年份的利率在 0.5% 到 1% 之间。武装冲突地区的比率可能更高。女性多于男性。
至少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已经记录了与创伤相关的精神障碍的症状。一些创伤后疾病的证据被认为存在于 17 和 18 世纪,例如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他描述了 1666 年伦敦大火后的侵入性和令人痛苦的症状。在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情况以各种术语而闻名,包括“炮弹休克”和“战斗神经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词在 1970 年代开始使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诊断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1980 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II)中正式承认它。
症状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通常在引发创伤事件后的前三个月内开始,但可能要到数年后才会开始。在典型情况下,PTSD 患者持续回避与创伤相关的思想和情绪,或对创伤事件的讨论,甚至可能对事件失忆。然而,个体通常通过侵入性的、反复的回忆、重温创伤的分离事件(“闪回”)和噩梦(50% 到 70%)来重温该事件。虽然在任何创伤事件后出现症状很常见,但这些症状必须在创伤后持续到足够程度(即导致生活功能障碍或临床痛苦程度)超过一个月才能被归类为 PTSD(临床上显着的功能障碍或创伤后不到一个月的痛苦可能是急性应激障碍)。一些人在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后经历了创伤后的成长。
相关医疗条件
除了 PTSD 外,创伤幸存者还经常出现抑郁症、焦虑症和情绪障碍。
物质使用障碍,例如酒精使用障碍,通常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时发生。当物质使用障碍与 PTSD 共存时,可能会阻碍从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其他焦虑障碍中恢复,或者病情恶化。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改善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焦虑水平。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情绪调节困难(例如情绪波动、愤怒爆发、发脾气)与创伤后应激症状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与年龄、性别或创伤类型无关。
风险因素
被认为处于危险之中的人包括战斗军事人员、自然灾害的受害者、集中营幸存者和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从事使他们遭受暴力(如士兵)或灾难(如紧急服务人员)的职业的人也处于危险之中。除了在银行、邮局或商店工作的人外,其他风险较高的职业还包括警察、消防员、救护人员、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火车司机、潜水员、记者和水手。
创伤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广泛的创伤事件有关。创伤事件后发展为 PTSD 的风险因创伤类型而异,在遭受性暴力 (11.4%),尤其是强奸 (19.0%) 后风险最高。男性更有可能经历(任何类型的)创伤事件,但女性更有可能经历可导致 PTSD 的高影响创伤事件,例如人际暴力和性侵犯。
机动车碰撞幸存者,包括儿童和成人,患 PTSD 的风险增加。在全球范围内,大约 2.6% 的成年人在发生非危及生命的交通事故后被诊断出患有 PTSD,并且类似比例的儿童患上了 PTSD。对于危及生命的车祸,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4.6%。女性更有可能在道路交通事故后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无论事故发生在儿童时期还是成年期。
已经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研究了创伤后应激反应。儿童的 PTSD 发病率可能低于成人,但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症状可能会持续数十年。一项估计表明,在发达国家的非战乱人群中,患有 PTSD 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比例可能为 1%,而成年人的这一比例为 1.5% 至 3%。平均而言,16% 暴露于创伤事件的儿童会发展为 PTSD,这取决于暴露类型和性别。与成年人口相似,儿童 PTSD 的风险因素包括:女性、遭受灾害(自然或人为)、消极应对行为和/或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系统。
预测模型一致发现,童年创伤、慢性逆境、神经生物学差异和家庭压力源与成年创伤事件后的 PTSD 风险相关。很难找到一致的预测事件方面,但创伤后分离一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发展的相当一致的预测指标。创伤的接近程度、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都会产生影响。据推测,人际创伤比非个人创伤引起的问题更多,但这是有争议的。遭受身体虐待、身体攻击或绑架的人患 PTSD 的风险会增加。遭受身体暴力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亲密伴侣暴力
暴露于家庭暴力的个体易患 PTSD。然而,暴露于创伤性经历并不自动表明一个人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怀孕围产期经历过家庭暴力的母亲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展与此密切相关。
那些经历过性侵犯或强奸的人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PTSD 症状包括重新体验攻击、避免与攻击相关的事情、麻木、焦虑增加和惊吓反应增加。如果强奸犯限制或约束该人,如果被强奸的人认为强奸犯会杀死他们,被强奸的人非常年轻或非常老,并且如果强奸犯是他们认识的人,则持续出现 PTSD 症状的可能性会更高. 如果幸存者周围的人忽视(或不知道)强奸或责备强奸幸存者,持续严重症状的可能性也会更高。
与战争有关的创伤
服兵役是发展 PTSD 的风险因素。大约 78% 的战斗人员不会患上 PTSD;在大约 25% 的发生 PTSD 的军事人员中,其出现延迟。
由于暴露于战争、苦难和创伤性事件,难民患 PTSD 的风险也增加了。难民人口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从 4% 到 86% 不等。虽然战争的压力影响着每一个人,但流离失所者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与难民的整体心理社会福祉有关的挑战是复杂的,而且每个人都存在细微差别。由于过去和持续的创伤,难民的幸福感降低,精神痛苦的发生率很高。受到特别影响且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的群体是妇女、老年人和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难民人口的创伤后压力和抑郁症也往往会影响他们的教育成功。
爱人的意外死亡
亲人突然意外死亡是跨国研究中报告的最常见的创伤事件类型。然而,大多数经历过此类事件的人不会发展为 PTSD。世卫组织世界心理健康调查的一项分析发现,在得知亲人意外死亡后,患 PTSD 的风险为 5.2%。由于这种类型的创伤事件的高流行率,亲人的意外死亡约占全球 PTSD 病例的 20%。
危及生命的疾病
与 PTSD 风险增加相关的医疗状况包括癌症、心脏病发作、和中风。 22% 的癌症幸存者出现终生 PTSD 样症状。重症监护病房 (ICU) 住院治疗也是 PTSD 的危险因素。一些女性从与乳腺癌和乳房切除术相关的经历中经历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有危及生命的疾病的亲人也有患 PTSD 的风险,例如患有慢性疾病的孩子的父母。
与怀孕有关的创伤
经历过流产的女性有患 PTSD 的风险。与仅经历一次流产的人相比,那些经历过后续流产的人患 PTSD 的风险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可能发生在分娩后,如果女性在怀孕前经历过创伤,风险会增加。产后 6 周时,正常分娩(即不包括死产或严重并发症)后 PTSD 的患病率估计在 2.8% 到 5.6% 之间,产后 6 个月时,这一比例降至 1.5%。PTSD 的症状在分娩后很常见,患病率为 24-30.1%在六周时,在六个月时下降到 13.6%。紧急分娩也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
遗传学
有证据表明,对 PTSD 的易感性是遗传性的。大约 30% 的 PTSD 变异仅由遗传引起。对于在越南作战的双胞胎,与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相比,患有 PTSD 的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与同卵双胞胎患 PTSD 的风险增加有关。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海马体较小的女性在发生创伤性事件后可能更容易患上 PTSD。研究还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其他精神疾病有许多共同的遗传影响。恐慌症和广泛性焦虑症和 PTSD 共享 60% 的相同遗传变异。酒精、尼古丁和药物依赖共享超过 40% 的遗传相似性。
已经确定了一些与后期 PTSD 发展相关的生物学指标。增加的惊吓反应和只有初步结果的较小海马体积已被确定为可能增加患PTSD 风险的生物标志物。此外,一项研究发现,白细胞中糖皮质激素受体数量较多的士兵在经历创伤后更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病理生理学
神经内分泌学
当创伤事件导致过度反应的肾上腺素反应时,可能会出现 PTSD 症状,从而在大脑中产生深层神经系统模式。这些模式可以在触发恐惧的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持续存在,使个人对未来的恐惧情况反应过度。
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引起大脑和身体的生化变化,这与重度抑郁症等其他精神疾病不同。与诊断为临床抑郁症的个体相比,被诊断患有 PTSD 的个体对地塞米松抑制试验的反应更强烈。
大多数患有 PTSD 的人在尿液中表现出低分泌皮质醇和高分泌儿茶酚胺,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比率因此高于可比较的未确诊个体。这与规范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形成对比,其中儿茶酚胺和皮质醇水平在暴露于压力源后都会升高。
脑儿茶酚胺水平很高,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 浓度很高。总之,这些发现表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PA) 轴异常。
恐惧的维持已被证明包括 HPA 轴、蓝斑-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以及边缘系统和额叶皮层之间的连接。HPA 轴协调激素对压力的反应,激活 LC-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与创伤后发生的记忆过度巩固有关。这种过度整合会增加一个人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杏仁核负责威胁检测以及作为对威胁的反应而进行的条件性和非条件性恐惧反应。
HPA 轴负责协调激素对压力的反应。鉴于PTSD 中对地塞米松的强烈皮质醇抑制,HPA 轴异常可能基于皮质醇的强烈负反馈抑制,这本身可能是由于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敏感性增加。PTSD 已被假设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学习途径,通过过敏、反应过度和反应过度的 HPA 轴来恐惧反应。
低皮质醇水平可能使个体易患 PTSD:在战争创伤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服役的服役前唾液皮质醇水平低的瑞典士兵比服役前水平正常的士兵在战争创伤后出现 PTSD 症状的风险更高. [101]因为皮质醇通常对于在应激反应后恢复体内平衡很重要,人们认为皮质醇含量低的创伤幸存者会经历一种控制不佳的反应——也就是说,反应时间更长、更痛苦——为 PTSD 奠定了基础。
人们认为蓝斑-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介导了恐惧记忆的过度巩固。高水平的皮质醇会降低去甲肾上腺素能的活性,并且由于 PTSD 患者的皮质醇水平往往会降低,因此有人提出,患有 PTSD 的人无法调节对创伤性压力增加的去甲肾上腺素能反应。侵入性记忆和条件性恐惧反应被认为是对相关触发因素的反应的结果。据报道,神经肽 Y (NPY) 可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并已在动物模型中证明具有抗焦虑特性。研究表明,患有 PTSD 的人表现出 NPY 水平降低,这可能表明他们的焦虑水平增加。
其他研究表明,患有 PTSD 的人的血清素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这会导致常见的相关行为症状,如焦虑、反刍、易怒、攻击性、自杀和冲动。血清素也有助于稳定糖皮质激素的产生。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多巴胺水平会导致症状:低水平会导致快感缺失、冷漠、注意力受损和运动障碍;高水平会导致精神病、激动和不安。
几项研究描述了 PTSD中甲状腺激素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浓度升高。这种类型的 2异能适应可能有助于增加对儿茶酚胺和其他压力介质的敏感性。
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的高反应性也可能由持续暴露于高压力引起。前额叶皮层去甲肾上腺素受体的过度激活可能与 PTSD 患者经常经历的闪回和噩梦有关。其他去甲肾上腺素功能(对当前环境的意识)的降低会阻止大脑中的记忆机制处理经验,并且人在闪回期间所经历的情绪与当前环境无关。
医学界对 PTSD 的神经生物学存在相当大的争议。2012 年的一项审查显示皮质醇水平与 PTSD 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大多数报告表明,PTSD 患者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水平升高,基础皮质醇水平降低,地塞米松对 HPA 轴的负反馈抑制增强。
神经解剖学
对结构 MRI 研究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与总脑容量、颅内容量和海马、岛叶皮质和前扣带回的容量减少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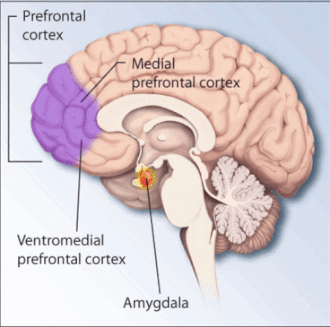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闽公网安备 35020602002465号
闽公网安备 35020602002465号